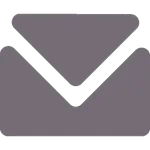「勉強的人不快樂
快樂的人那就是我
你也想跟我一樣
雨下起來唱了首歌」
高中畢業時,得到了一支鋼筆,它裝在絲絨的盒子中,銀灰色的筆桿鐫刻著一行德文,儘管不懂行文的意思,卻隱隱觸到大人與孩子的邊界。
家鄉那邊的畢業典禮與臺北略有差異, 18 歲的夏天會在一場莊重浮誇的晚宴下開啟,大家被裝進不合身的禮服中,嘗試搖晃高腳杯中的軟性飲料,搖搖擺擺地向老師謝酒,開始口是心非地說出一些詞藻,而晚宴就在爭辯用餐禮儀的過程中徐徐落幕。
似乎學習大人的姿態,是那個社會耳提面命的第一句話;零散的青春日記到了裝幀的時刻,卻驚覺自由所剩無幾。
那時的自己總想著,安放十八歲靈魂的他方,必定在海的那頭。
「遠方 遠方 哪裡才是遠方
原來 愛人不在身邊就叫遠方 遠方
還好我愛的人永遠住在我心臟」

我總愛形容遠方是一種追求的語境,而這種語境不僅有理想的生活型態,也包含著一份信仰,因此不曾想過,活在這種語境下的自己會成為語意不詳的存在。
各種文化差異似劣質的成衣,總有些線頭露在外面,總有些扣子洞難以打開。
失眠、胃病、濕疹是這個島嶼向我發出的首個警訊,那時候,一週約有三四天是完全無法入睡的,試過搜尋各種助眠的音樂和影像,結果都是徒勞無功,只能暴力地熬過日間的睏意,逼自己到適當的時刻再入睡。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陸陸續續用了好多年,直到現在,難以入睡的問題依然存在。
也許是靈魂缺失了某種安全感,被自動壓抑的情緒只能在晚間抒發,那段日子總是很喜歡向舊友抒情。愛這個字是那麼難以說出口,但當你隻身在外時,卻總是會覺得時間不足夠,曾經一同邁向前的道路逐漸分岔,再不好好地道謝,大家便長大了,再來說愛似乎會變得唐突。
很多人會說,好朋友是不會因為距離而改變的,的確,美好的記憶會封存、發酵,隨著日子過去,在充滿挑戰的成年世界中,那段回憶只會成為香醇的美酒。但同時,那種不願再多言個人煩惱、不願朋友擔憂的著想也會越來越多,漸漸,情感沒有生出空隙,距離卻開始拉遠。
「長大後誰不是離家出走
茫茫人海裡游
抬起頭才發現 流眼淚的星星正在放棄我
請擁抱我 萬一我不小心墜落」

適應大人的過程,有段時間罹患了某種疾病,好幾次處於崩潰的邊緣。某次回家,走在熟悉的捷運站,由上層出口望下看時,密密麻麻的人群像融化的奶油,開始化開、混合;筆直的線條開始扭曲、蜿蜒。雖然只是一霎那,可每當走入人群密集的地方,這段影像就會在腦海中揮之不去。
有點厭倦自己,有點怨憤世界,是那時期內心最大的感受。與朋友相聚時他們總問我,為什麼看上去不開心、為什麼臉上沒有笑?情緒與表情被分得很開,適當的表情再也沒有出現過,取而代之,不恰當的情緒總顯露出醜相,敏感的神經一觸即發。那段日子,除了文字、音樂、兔兒,再沒有能讓人開心起來的事物。
有人跟我說,抑鬱症就像過敏,它永遠有可能再爆發,即便你小心翼翼地躲避已知的過敏源,情緒的活火山總需要釋放的一天。
成為大人的日子,與離開孩童的日子相比,似乎在「大人」的年資下自己還在學童階段,那些灼熱的情緒也在近年冷卻下來,儘管世界還是不可愛,但也開始摸索出適合自己的大人模樣。
🖋駐站作者:鍾粹